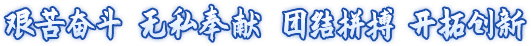作者:丁辉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5-4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政治气候的宽松,对五四的研究开始出现“众声喧哗”的局面。关于五四的研究不再是既有的“政治结论”一统天下,这自然是好事情。然而,随着五四研究“多元”言说时代的到来,五四这个历史符号也愈加暧昧难明,五四这一段历史也有被搅成历史糊涂账的危险。
1996年,海外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林毓生到上海访学。在一次有众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会的演讲中,林毓生被问及“如何继承五四遗产”的问题。大家就是大家,林毓生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一语解纷,一言息讼,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困扰了中国学界多年的问题。林毓生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把五四这个价值符号分成三个层次:五四的口号;五四的理念;五四的精神。林先生的结论是:口号可以商榷;理念可以批评;但五四的精神不能丢弃。
那么,五四精神的内涵有哪些?或者说,我们今天必须继承的五四精神遗产都有哪些层面?我尝试把五四精神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民主精神;科学精神;人道精神;个人主义;自由精神;独立精神;批判精神。
五四的诸般精神取向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史的洪流中历经沉浮,命途多舛,其中亦多有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者。比如“民主精神”:国民党统治时期,“训政”阶段一再延宕,“民主”的兑现终至无期。再比如“人道精神”:我们竟然有漫长的几十年谈“人道”色变,“人道主义”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似乎我们社会主义可以不讲“人道”似的。“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冲突究竟在哪里?我后来终于想明白了:人道主义发展到比较高的境界的时候,是把敌人变成人;革命发展到极端状态的时候,则正相反,是把人变成敌人……其他举凡“科学精神”、“自由精神”、“独立精神”、“批判精神”,有的固然可以说曙光初现,有的则依然是我们的“仲夏夜之梦”。
有人会提出疑问:你似乎漏掉了五四的“爱国精神”?应该说提出这样的疑问是正常的,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五四这个价值符号究何所指?我们今天谈五四,其实是有两个路径的:一是指五四运动;一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用五四来命名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那是自然之事;唯独后来用五四来冠称“新文化运动”难免启人疑窦: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本来分属于不同的价值谱系。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当然有它的“政治关怀”;而新文化运动则自然不能说没有它的“政治关怀”,但更主要的毋宁是它的“文化关怀”与“知识关怀”。也许是我“小人之心”,我一直觉得把新文化运动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许正是为了用“爱国”来遮蔽(回避)新文化运动更具普世色彩的其他诸般价值主张。
正如因为约定俗成,我们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说法,同样是约定俗成,我们今天谈五四,所指已经不是作为学生爱国运动的五四运动,而是发端于1915年,延续至20年代早期的新文化运动。我们所说的“五四精神”严格讲来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如果一定要新文化运动也“爱”什么的话,与其说它是“爱国”的,毋宁说它是“爱真理”的。换句话说,五四先驱是通过“爱真理”来爱这个国家的;当“爱国”与“爱真理”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五四先驱定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可以拿来作为佐证的是胡适的一件事。1933年,日寇步步紧逼,形势危如累卵。有董姓者在《大公报》上发表“爱国”高论,称正好利用百姓的“无知,好对付,肯服从”,拉他们的伕,尽他们的所有供给军需,让他们去堵日寇的枪眼。针对如此“流氓爱国”的论调,五四先驱之一的胡适态度鲜明,他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言:“如果这才叫爱国,亡国又是什么。”
19世纪俄罗斯思想家恰达耶夫说:“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来热爱祖国”,“我首先用真理为祖国承担义务”。这些饱和着痛苦的爱的文字或可移用过来作为五四一代关于国家的立场。
《中国科学报》 (2012-05-04 B4 作品)